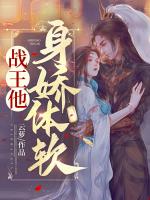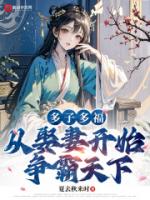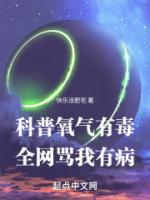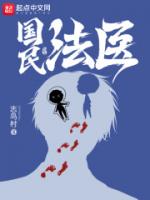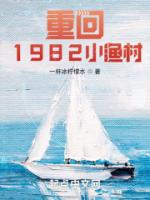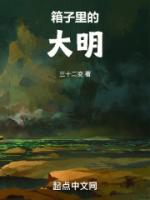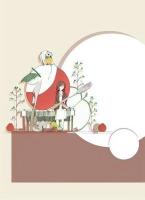江阳郡署,春寒未散,朝雾弥漫。
苏砚尚未进仓,便听闻一则消息传遍郡中——“章泽参李封一案,未被准奏,回文仍悬。”
原本章泽赴东营巡视,只为调阅旧年粮册,查账补数,却在途中上呈奏章,拟参李封“仓制不明、放纵吏胥、延误上仓”,谁知郡守府尚未批复,消息却已走漏,传至市井。
有人说,这是章泽故意放风,以震慑郡中残余旧势。
也有人说,是李封反设阳谋,故意放出风声,引人议论。
无论真伪,仓中数人却顿时生出警惕。
—
主账位置,如今已无人敢言轻视。苏砚每日入仓,简伯虽仍冷言,却不敢再露轻蔑之色;虞忠虽未亲近,却屡次将重账交予其批;唯独言如清,仍旧独来独往,时而沉思,时而旁观,偶有只言片语,却都不落痕迹。
苏砚自知,这是“危权”之职。
他越是接近权谋之核,就越明白这不是一场“为善者得赏”的博弈,而是——“最无名者,最易被牺牲。”
仓中暗流涌动,却在第三日彻底爆发。
那日未时,李封府中派来一名主簿,唤作徐蕴,带着郡守手令、文符印帖,宣读:
“因查账事疑,有人托名查仓,暗批风语,意涉郡政,需带主账苏砚入府一问。”
仓内顿时静若死地。
徐蕴面色冷峻,语气温和却不容置喙。言如清第一个抬头,看了苏砚一眼,却未发声。
苏砚起身,淡然一揖:
“愿往。”
他知道,这一刻,终于来了。
三日前的“批语”,章泽不批,却未作声,今日李封借势出手,既可问罪,又可试探;若苏砚退缩,仓中信任尽毁;若苏砚强行抗命,章泽亦难再保。
他随徐蕴而行,走出仓堂,踏上郡署正道。
天光初暖,石阶浮尘,风声犹如刀起,斜斩衣角。
—
郡守府前厅,李封坐于堂上,青衣而不佩印,案几不设笔墨。
这是“私审”。
苏砚立于阶下,未语。
李封静静看了他片刻,忽而一笑:“你瘦了。”
苏砚不应,只作揖。
“那一场病,听说连命都保不住。如今却能主仓修账,还写出句句惊心的词句……你可真是‘苏砚’?”
他语带试探,却未直接责问。
苏砚低头答:“正是。”
“你那句‘今地不存,则账虚也’,若为戏言,我不计较;若为揭事,我却不能不问。”
苏砚目光沉静:
“郡守之言,砚谨记。”
“那你且说,三年前蓁仓未废,汝阴旧账所录尚属实;你怎敢在其后落下‘账虚’二字?你可知此言若为实,则郡署上下多有失察?若为虚,则你意涉毁人清誉?”
苏砚心中已然有数,抬头一拱手,道:
“砚所批者,非断语,乃探语。”
“探什么?”
“探真。”苏砚道,“郡中有事,自有上官裁断。砚不妄议人,只敢议账;账中若有误,求改;若无误,愿受责。”
李封一怔,随即笑出声来:
“好一个‘只议账、不议人’。你倒聪明得很。”
他将手中印章抛回案上,起身负手而立:
“章泽参我一案,你知否?”
苏砚平静答道:“听闻。”
“你可知,他将你所批诸语,俱封入卷宗?那一纸‘今地不存’,就是你的文字。”
苏砚略一颔首:
“所批皆为实情,字字留有出处;砚未言人,但求自清。”
李封看着他,良久,缓声道:
“苏砚,江阳郡不喜生事者。章泽,也不过是魏王新近提拔的一柄利刀。你要在此谋生,须知如何藏锋。”
苏砚拱手,不卑不亢:
“砚为质子,不敢妄言利器之事。只知人活世间,当求无愧。”
李封面色一冷:“你是质子?”
“那为何可主仓?为何可批政账?为何章泽敢让你议案参官?!”
苏砚依然未动,缓缓答道:
“因砚,不惧死。”
这一句,不是戏言。
他是真不惧死,在穿越而来、睁眼那一刻起,他就知道:
若不敢搏命,便只配等死。
李封凝视他良久,终是一声冷哼,挥袖而去。
“既如此,那便让你再活几日。”
“仓账你接着批,莫再写‘风语’;再有一字惊人,休怪本郡不留。”
苏砚长揖到底:“谨记。”
待其走后,徐蕴上前低声道:
“章使命我言:‘水未净,勿踏深池;人未醒,莫破梦境。’”
苏砚微怔,随即点头。
他明白了:章泽已察觉他试探之意,但还不愿让局彻底翻开。
此时不宜再揭蓁仓旧案;可批,可查,但不能“点破”。
就像一盘棋,不可贸然吃掉对方棋子。对方或许故意示弱,只待你落入陷阱。
—
离开郡守府后,天已大亮,街上渐热,百姓喧哗声渐起。
苏砚站在高阶之下,看着晨雾散去的江阳街巷,忽而笑了。
“藏锋...也好。”
他低声自语:
“藏不是避,是将锋藏入鞘,只等一击必杀。”
他转身,重新回仓。
⸻
回仓当日,苏砚无言。
他未言李封如何发问,也未言章泽是否回应,只照旧坐在主账位上,翻阅新送的账册,一页页写下批语,一笔不漏,却字字含锋。
但仓中其余三人,却各怀心思。
虞忠第一个开口。
他将一卷仓籍掷在案上,沉声道:“这是上月多出的二十石米账,你不是主账么?来批一个。”
苏砚没看他,只翻账自顾批阅。
虞忠冷哼:“怎么,不敢?”
苏砚写完最后一笔,合上账册,才缓缓看向虞忠:“此账既无供货方,也无验仓文,若我批了,便是空印;若我不批,你便说我推责。虞修吏,你到底是想要我查账,还是要我背罪?”
虞忠脸色一变,刚欲发作,简伯却在一旁插话:
“我记得这批账,去年其实就提过一次。那时说是‘因兵急调’,但后来又没人认领。如今却又冒出来一份,真当主账是傻子?”
他说完,看了苏砚一眼,嘴角微动,似笑非笑。
苏砚会意,轻轻一拱手:“多谢简修吏提醒。”
简伯摇头:“我是怕你死得快。”
虞忠冷笑:“主账好气魄,一朝被扶,便敢骑在老吏头上。章使真是慧眼识珠。”
他这话已近乎明讽,但苏砚毫无波澜,淡淡说道:
“我若不批,便是避事;我若批了,便是护错;所以我不会批,但我会附文。”
“附什么文?”虞忠皱眉。
苏砚提笔,在账册空页落字:
“无供无文,账属虚;但见仓不空,实物未缺,或为前调后补,或为旧账未清。若有异动,当查库实,以对数名。”
他写完,举笔而停,望向虞忠。
“你是副仓主,愿随我一道查仓么?”
此言一出,虞忠竟语塞。他本以为苏砚不过书生一介,不会主动下场,谁知对方反客为主,居然要他“共同查仓”。
这若应了,便是同担风险;若不应,便等于默认账目有鬼。
简伯笑了:“去吧,老虞,这可是你给他递的刀。”
虞忠面色阴沉,拂袖而去,不发一言。
—
次日清晨,苏砚便携章册直入北仓。
此仓为“民粮专仓”,所存粟米大多由地方缴纳,与“军粮、使仓”分属两条线,极少有人过问。
他翻查三批仓封,按册验仓,果真在仓角堆垛下发现一批未入账米袋,封签残缺,却隐有“乙亥年初”字样。
他心中一紧。
乙亥年,正是三年前。
而这批米袋若真属旧藏,则极可能与“蓁仓”有染。
他未声张,命人将此批封存,交由章泽审批,却只留一句话给简伯:
“此账若查,便需查透;若不查,我便认账。”
简伯狐疑:“你当真敢认?”
“我为何不敢?”苏砚平静一笑,“查不得真账,便认虚账,这是你们定的规矩。只不过,我会记下,是谁让我认的。”
简伯不语。
—
午后,仓署忽来一名陌生老者,自称“郡中簿曹赵史”,衣袍斑驳,却佩着旧式铜章,一进门便道:
“主账何在?我奉郡命,前来查库核封。”
苏砚抬眼打量,未见印牍,但也不动声色,笑道:“赵史远至,有失迎候。仓中在校账目,未请指教所查何项?”
“你批那句‘今地不存’,我不喜。”赵史冷声道,“三年前我还在蓁仓理库,那地儿不是你一笔可以抹去的。”
苏砚心头一震,面上却无惧色:“那便请赵史以旧例正新错,砚愿随学。”
赵史皱眉:“你这小子,不怕我翻你的旧底?”
“请赵史便翻。”苏砚拱手,“若我一笔抹掉了赵史三年旧勤,那是我之过;可若那一仓本就是空的,那我不过是说了句实话。”
赵史盯着他许久,冷哼一声,拂袖而去。
苏砚送其离去,返身落座,心中却已明了:
此人并非真正奉命查账,而是李封试探的又一枚“暗子”。
他若是怕了,便会收笔;若是强了,便会招祸。
可这世上,从无“完美之计”。
真正的谋主,从不指望无祸,而是学会选祸。
他望着桌上的账册,一页页翻过去,手指停在那句熟悉的评注上:
“旧仓为障,三年之账皆虚;若再往前索十页,或可得其人。”
他轻声一笑,念出心中未写下的那一句——
“十页之后,是命;十页之前,是局。”
⸻
黄昏时分,仓内渐暗。
苏砚伏案阅卷时,忽有脚步声至,一名年幼仓役匆匆入内,将一封卷简放至案上,低声道:
“是言主吩咐奴送来的,说是‘旧仓库旧账本’,叫主账看时小心些。”
说罢,便低头快步退下。
苏砚取起书卷,一眼便见封口用的是极旧样式的“郡中封火”,而印泥早已干裂,想来并非近年之物。
他心中一紧,随即轻撕封口,缓缓展开。
这并非普通账目,而是一本**“仓役名籍”**,上标“乙亥年末·蓁仓值役”。
眉目之间,名字密密麻麻,俱为三年前蓁仓在籍之人,籍贯、身份、任期、去处,俱有记载,甚至标注是否“结账完清”、“临时调任”。
他迅速翻看,忽然停在一页。
“朱敛,籍贯阳狐,入仓时间:乙亥年十月,任期三旬。去处:不明。”
去处,不明?
此为仓中之大忌。尤其仓役出入军粮仓,若不明去向,便极可能与私运、盗贼、私卖有关。
但此人名字旁,却有一行极细小字迹,以异墨写就:
“已遣还,不录。”
苏砚眉头微皱。
“遣还”与“不录”,乃典籍之矛盾语。
若遣还齐地,便必有交接;若不录,则无凭无证。此言之下,便如将人“从账册上抹去”一般。
而在这本旧籍之后,还有一页残存纸片,被人压在最后。
他轻轻揭开,见其字迹斑驳,隐约可辨“仓中夜祟”、“有贼夜入”、“失米不报”数字,字句凌乱、似为草记。
他眼神一凝。
若连“祟贼”皆录,说明仓中当时确有“夜盗”传言;而这些传言,如今俱被压下,不见于任何正式档案。
“朱敛......夜盗......未报米差......”
他低声重复,脑中已将这些碎片串联——
这朱敛,极可能是‘失米’真正的交接人之一,亦或是‘替死者’。
蓁仓三年前的粮案,根本不是“空仓误记”,而是——
人为销账,后人补错,再人补盖,层层造伪。
这朱敛,或是漏洞起始之处。
—
次日,苏砚未将名籍上交,而是带着简伯查仓。
北仓后排墙角,有一批标记为“调余之粮”的陈袋,外观皆完,封绳未动。
简伯瞥了一眼,冷声道:“这批去年也见过,说是未用旧米。你也信?”
苏砚却不作答,只蹲下身,从袋底抽出两指米粒,举到阳光下观之——米色发灰,混有极细沙尘。
“若去年之米,为何混沙?仓规明言,凡米入库,先淘三遍,晒干封袋。这批若是新封,怎会如此?”
简伯眼神一动:“你是说——”
“我什么都没说。”苏砚放下米粒,轻声道:“我只是疑惑,三年前的蓁仓旧米,为何还能在账中见到名字?”
简伯盯着他:“你究竟想查什么?”
“真相。”
“还是权力?”
苏砚转头,看着他,神情一如既往的平静。
“若真相能换权力,那便最好;若不能,那也总比,连真相都没人要强。”
简伯半晌无语,忽然低声道:
“章泽不可信,李封亦不可信。你若真想活,别两边都得罪。”
苏砚笑了笑:
“得罪人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,到最后谁都不怕你。”
—
入夜,他将那份名籍封入一只油布包中,悄然放入偏阁木柜下。阿彤在外打水,看见他略显紧张,低声问:
“公子,可有事?”
“无事。”他温和一笑,“只是想起老家也常查账,翻旧纸也翻得手疼。”
阿彤端着水走过来,递给他:“今儿仓中有没有人欺负你?”
苏砚接过,轻声一笑:“现在欺负我,也得想一想值不值得了。”
阿彤一愣,随即点头笑了:“那公子就是越来越厉害了。”
他未接话,只是仰头喝了一口水,仿佛将满腹心事吞进喉中。
他心知:
这一份“朱敛”的名册,不仅仅是粮案的一角——它极可能通往三年前郡中某场***的真相。
而这风波,也许就是他今日即将陷入的深渊。
但他不怕。
他在现代就是个查资料的书生,埋首纸堆多年。
如今他仍在查,只不过这回,纸下是命,是局,是刀,是权。
是未来。

 连载中
连载中